詩歌單元:用詩歌推開迷途
實踐活動周詩歌單元安排了兩場沙龍和講座。
1、 黃禮孩、世賓、譚暢——用詩歌推開迷途

黃禮孩用三個關鍵詞“理想、召喚、執行”對自己接下來分享的内容做了簡要概括:因為有了理想,詩人才能有噴薄的熱情想要去抒發内心所感所思;懷揣着讓“古漢語喚醒當下的可能性”的願望,希望通過詞語的重新搭配、組合來應對世界的雜音、過濾掉塵世的雜質,通過聆聽來自遠方、天上以及内心的聲音來對接寰宇,使世界變得更好;每個人都需要通過“執行”來改變自己。

世賓從自己的詩歌《光從上面下來》論述人的生命狀态,認為面對生命的障礙,每個人需要有詩興、戰鬥性以及對所有美好事物的堅持,“唯有這樣,生命的詩性才能打開。”

譚暢則從女性身份的社會曆史地位出發,講述女性這種身份符号是一種被貶損的社會現象,再舉美國的禁酒等與女性運動有關的例子表達随着社會的發展,“女性不僅不會被貶損,還沾了光,例如lady first”,今天我們需要正面面對“女性”這個詞,因為21世紀是女性的主場,同時女性也要擔負起相應的社會責任。
楊克——詩歌:欲說還休的想象之聲

“詩寫的不是一種概念,而是一種意象”,缺乏意象且泛濫概念,正是許多初寫詩的人易犯的錯誤。楊克說,詩人不是一種身份,而是一種詩歌的聲音,文學性其實就是一種腔調,語言給人以文學性的感覺。來源于民歌的詩歌,更應該注重語音語調,如蕭紅認為“處處”好聽,在于它不是到處,不是各處;海子的“從明天起”,謝有順解讀是一種清空今天的悲觀,但也很可能是比起“從今天起”,詩人選擇了更動聽的“從明天起”,是詩人的無意識;而魯迅曾經寫:“我家院子裡有兩棵樹,一棵是棗樹,另一顆,也是棗樹。”乍看啰嗦,實際上放緩了視覺移動的速度,準确傳遞了作者凄婉的心境。楊克說,翻譯也是在創造,它失去了一些,但也創造了很多,有時候,二流文學能翻譯成一流的,有時候,一流不慎也能翻譯成三流作品,但無論如何,詩歌翻譯是麻煩的。中國古典詩歌的魅力在翻譯上就無法呈現,令人惋惜。楊克最後鼓勵詩人們:創作詩歌是爬五嶽,有人爬泰山,有人登華山,每個人把自己的那座山爬到頂峰,就是極緻。
小說單元:與文學進行有限溝通和無窮對話
實踐活動周小說單元安排了五場沙龍和講座。
1、 王十月、王威廉——一個與文學進行有限溝通和無窮對話的夜晚

(前左:王十月;前右:王威廉)
王十月講述自己的創作經驗,如果想寫某個題材,就要先考慮它是否被許多偉大的作家寫過,自己能否寫得更新、更好,“如果你能想出一個非常天才的構思,那麼你怎麼寫也差不到哪裡去。”王十月用“清蒸魚”和“臭鲑魚”做比喻,“如果這個食材已經不新鮮了,那就把它做成臭鲑魚。”并以自己的小說《罪人》為例,認為要走出偉大的陰影,最好是反着寫,并且要貼着時代與國情寫。至于寫法沒有高下之分。魯迅為揭除弊病而寫,所以删繁就簡,他的小說“是鐵一樣的,冷的,硬的。”卡爾維諾在圖書館待了一輩子,看了太多書,如果讓他去寫底層的農民,他未必能寫好;沈從文的寫作是為了建希臘小廟供奉人性;汪曾祺是要“人間頌小文”,故其作品沒有大悲歡。“這些能寫進文學史的作家,最初沒有一位是抱着史上留名的目标去寫的。”
王威廉說,寫作是每一個人的權利,是文學最終讓我們理解了情懷。他在哲學中第一次徹底認識到,自己是無法從死亡中幸免的,因為“哲學是面向死亡的練習。”他認為,這對每個人的生命都是一個關鍵時機:清晰地面對死亡,“這樣的時刻,就是文學的時刻。”王威廉指出,要當好作家,既要有直接的日常生活經驗,更要有間接的他者經驗。而互聯網時代,一切都可以互聯,經驗在貶值,寫作在泛濫,這個時代對寫作者提出新的要求——對經驗的穿透能力與反思能力。寫作實際上還是在寫生活,它容納醜陋,但又留下希望與追問,“文學最終一定要有追問,追問什麼是更好的生活。”對他而言,文學就是不止步,不停地問為什麼,為什麼。文學就像一個容器,它是空的,放進去什麼,它就能變成什麼,它保留了生活中那些毛茸茸質地的東西。“文學讓一切無意義變得有意義。”
2、 鮑十——讀發乎于心的經典,寫發乎于心的作品

鮑十強調,寫作的關鍵在于閱讀,隻有經曆大量的閱讀,寫作才會有後勁兒,而一個人讀得最多的書,一定會形成其寫作的底色,因此這就涉及到“讀什麼”。鮑十認為,讀經典非常重要,因為它們經曆過一代又一代的淘洗。一個人的智力有限,要學會相信所有人的智力,經過淘洗還能流傳下來的,一定是好書。在鮑十老師家中,他的書房、客廳,以及兒子的房間,都堆滿了他購買的書,他甚至還與兒子在電話中探讨胡安·魯爾福的小說《佩德羅·巴拉莫》,受父親影響,兒子也從小讀了大量的書,并認為《佩德羅·巴拉莫》是他讀過的最好小說。而胡安·魯爾福正是加西亞·馬爾克斯極其推崇的作家。“總之,閱讀是重要的,讀什麼,也是重要的。”
鮑十認為,對一個作家來說,首要的問題是“你寫作圖什麼?”如果一個作家的寫作不是為了娛樂、發财或是留名,而是真的為了人類寫作,為人類的發展做貢獻,那麼他的寫作目标将會完全不一樣。好作家不是指全盤正能量的作家,而是有批判性的,關鍵要給人類帶來啟示。在鮑十看來,一個作家不需要寫的太多,但一定不能撒謊。其次,鮑十認為作家要保持自己。無論是獨立思考還是寫作風格。“一個作家要守住自己是很難得的,但汪曾祺守住了。”于他而言,與汪同時代的許多作家想通過寫作圖謀什麼,因此碰上不熟悉的題材也寫,不但無法用文學保留部分的曆史真相,更是讓作品充滿了尴尬。“作品不是隻有一個框架,它就像一個活着的人,一定要有血有肉,有疤有痘。”
他給出的重要建議是,要寫好作品,必發乎其心,要等到那個非常深的感動,等到不寫不行的時候再寫,那麼無論是在當下,對曆史還是對未來,都對得起作家這個稱号。
3、 陳崇正——我從沒有想過自己會當一個作家

“一個人寫作可能是快樂的,也可能是痛苦的。”陳崇正創作的過程比作“懷胎十月”,這個過程是長期的,需要慢慢醞釀、積累。在這漫長的創作過程中,創作者需要一個能支持其進行持久創作的環境,這樣的環境裡最重要的元素即是信心。這種信心既來自于外部的鼓勵,也來自于創作者内心的自我肯定與自我加冕。唯有具備充分的信心,才能持之以恒地進行并堅持創作之路。
在人類意識蒙昧階段,人們信任神;文藝複興後,人們開始崇拜人;到工業革命後,人們崇拜機器;信息時代,我們開始崇拜互聯網。因此,人類像崇拜神一樣,崇拜大數據的時代是有可能到來的。陳老師的“危言”包含着他對社會的關懷,表現出他對創作觀念與方式應不斷與時俱進的要求。
創作是對現實的展映,同時也是對現實的升華。《半步村叙事》帶着人們社會生活的影子,揭露了社會的多面性,但并不是對生活的完全照描。陳老師運用寓言式的藝術加工,使作品更具意味,也在由點及面中,涵括了世界最荒誕的一面。如作品中人物的“分身術”,可以讓一個人同時生活在平行時空中的不同階段;少年、中年、老年時空的人,同時瓜分着一個人的生命——“如果你能選一個階段生活,你會選擇在哪個階段?”這其中蘊含着深刻的哲理思考。
4、 申霞豔——為什麼讀經典:重讀《安娜.卡列尼娜》

申霞豔教授指出,在“快餐文化”及“碎片化”閱讀盛行的信息化時代,絕大多數的人很難做到心無旁骛地閱讀;而過多閱讀那些所謂的“快餐化”及“碎片化”文字,蠶食了人們對文學的鑒賞能力。這也讓我們愈發明确,靜下心來閱讀經典有助于挽回人們對文字的感覺與判斷。
《安娜·卡列尼娜》是一部社會百科全書式的作品,涵括了社會各階層的圖景,作品中的悲劇具有世界性的意義。卡列甯是“套子裡的人”,被習慣駕馭着,失去了生氣,反映了官僚制度對人精神的腐蝕;伏倫斯基需要事業與自由,他甯願為安娜開槍自殺而不願舍棄自由,這反映了人類精神的複雜性與欲望自身的繁殖能力之間的矛盾這一哲學問題——當人們得到了愛情後,便想它長久,而在欲望之間、價值之間,彼此是沖突的。正如叔本華所說的“鐘擺理論”——欲望不能滿足時是痛苦的,滿足之後便是無聊。
列夫·托爾斯泰的偉大之處正在于他能夠把控時代的脈搏。濃厚的時代氣息,加之以開闊的視野鋪展開叙事空間的手法,成就了他的經典之作——《安娜·卡列尼娜》。
5、 張甯——說不盡的魯迅

張甯教授認為,中國至少有兩個文學現象是說不盡的——《紅樓夢》和魯迅。盡管魯迅“希望自己的作品速朽”,但他的文學及其影響短期内還是無法消失,這不是我們這個時代的幸運,恰恰是這個時代的不幸。
張甯以研究魯迅數十年的經驗為提煉基礎,從魯迅思想中的“反傳統”“民族主義”“國民性憂思”三點出發,為我們修正被誤讀、被窄化的魯迅。魯迅撰文反駁,認為不該因憤怒而全盤否認西洋人的法律,其次,“人跟雞鴨不同,能組織,能反抗”,不該自己不努力,隻要求洋人改善處境。這被左翼作家廖沫沙斥為買辦思想。張甯由此引出A型民族主義和B型民族主義:A型是恥辱的、封閉的、排外的民族主義;B型是超越恥辱的、開放的、内斂的民族主義。魯迅所持的民族主義,屬于後者。
張甯教授說,租界有兩面性,一方面象征着恥辱,另一方面在戰亂年代又庇護過許多作家。魯迅的《且介亭文集》正是在租界中最便宜的閣樓“且介亭”寫就。魯迅一雙火眼,既肯定了租界的具體法律條款,又看清了國民性病症——哪怕在今天,大部分人依然和廖沫沙一樣,沒有看清。魯迅在其作品中反複書寫的主題之一是等級分明、欺軟怕硬的國民隐形心理;盡管遠在隋唐,中國已經廢門閥,興科舉,可分級的觀念深入骨髓,如趙太爺睚眦必報地恐吓七斤——剪辮子是要砍頭的;這和儒家“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思想是分不開的。
魯迅的革命氣質貫穿他的一生,但他的革命較其他人不同在于:一、防範新奴役的産生、跳出曆史的主奴結構,始終是他的革命背景;二、他計算着鮮血的代價,并以此衡量革命的性質。他有着自成一體的政治思想,張甯稱之為“民衆政治學”。魯迅本應該和許多同行一樣,站在社會的上面,但他始終堅持“從下邊看”“以文學為政治”,緻力于“讓民衆從政治的客體變成政治的主體”。
名句“無窮的遠方,無數的人們,都和我有關”,寫于魯迅死前一個月。張甯認為,讓魯迅發此感慨的,是他作為“一個無神論者”的“宗教意識”。這樣的宗教意識,讓魯迅擁有了别于日常生活的超越性。
編劇單元:電影,這場能成真的夢
實踐活動周中舉行了兩場影視編劇沙龍。
1、 張瓊——真善美是藝術的永恒标準

曾出品發行《我為車狂》《男神時代》《脫軌時代》《我們停戰吧》等影視劇的骅森影視董事長張瓊女士與同學們分享的是人生修養和職業儲備經驗。張瓊首先強調讀書的重要性,閱讀是創作前的必要準備,《紅樓夢》中的薛寶琴以讀書靜心養志,以步度量天下,不困于四角的天地,終在“萬豔同悲”的大境地裡得以善終。而在創作方面,閱讀為創作積累了素材,打下了良好的文化基礎;更重要的是,它為創作者提供了多角度看問題的視野和思維。
“真善美”并不是刻闆的教條,而是老祖宗傳下來的人生哲學和智慧。“真善美”中以“真”為先,因為真實和坦率能引起“善”和“美”。美則是一種代表普世價值觀的美,不是浮于表面,而是由内而發。她以剛剛拍攝完成投放在央視播出的廣告片《恒大童世界》為例,分解影視作品的言語美、視覺美、自然美等要素。
2、 鄭大衛——|電影: 這場能成真的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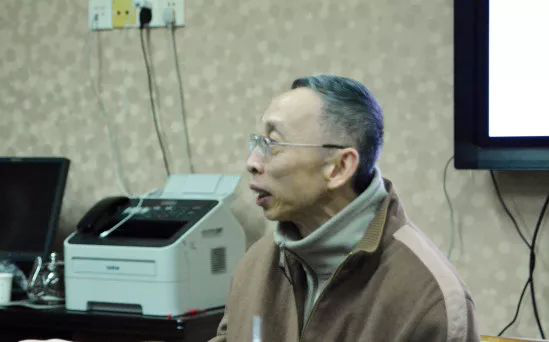
鄭大衛從自己三十餘年的從影經驗出發,以電影與其他文學創作的差異、電影故事的基本元素與形态以及類型電影的基本模式及其創新等為角度,引導同學們以一個專業電影人的視角,重新認識了電影故事與創作。
“電影是什麼?”鄭大衛在談及電影及其創作前,向在場的同學們抛來了一個非常司空見慣卻讓人疑惑不解的問題。鄭老師從不同角度給出了自己的解答:電影是一種産業,因其有專業的群體;電影是一種投資,因其需要金錢的支持;電影是一種創作,因其是才智貢獻的結晶;電影是一種技藝,因其需要專業技術的供應。除此之外,鄭老師還從各個群體(如官方、社會老闆、電影人等)的角度及電影的特點和社會功益等方面,全方位地賦予了“電影”一個明晰的定義。然而,從純理論及概念的層面抽離出來,鄭老師滿懷深情地說:“電影,可以是一個人的夢想。電影就是通過視聽影像在展示你的感覺與想象。”
鄭大衛強調,每個故事應有的主要元素(生存、死亡、困難、危險、食物、性、金錢等)及基本結構(事由、主角、目标、阻礙、幫助、平衡等)是相似的。為此,他舉了《魔戒》和《福爾摩斯》、《風中奇緣》與《阿凡達》等幾組對比例子,通過标注故事梗概中的元素及梳理故事的脈絡,讓同學們發現了每個相同的類型故事之間的共通及相似,充分說明了電影故事創作中具有基本型态的故事模型及相似的内容。“掌握電影故事創作中的故事基本型态和内容的相似性,就有可能幫助你在創作時,判斷出當前構思的狀況與已知狀況兩者基本形态的相似性,進而産生突破或得出某種結論。”鄭大衛進一步闡釋道。類型電影具有基本的創作套路、模式及方法,當我們學習、掌握了類型電影的創作套路、模式後,才有可能反套路、反模式、反方法與反走向。
創新創業單元:為平凡的人生注入不凡

本單元邀請了創業導師啟鈞主講。啟鈞談起自己創業的經曆來十分謙遜與低調。他坦言學生的首要任務是學習;創業是長久而艱難的事情。在啟鈞老師看來,創業道路上好的合夥人極其重要。對此,啟鈞表達了他對合夥人蒲荔子老師的贊譽。“蒲荔子是文學界譽為最優秀的青年作家之一,他是傳統文學向網絡文學過渡時期的人物,極具才華和熱情。他也是我見過的文化人或者說媒體人中非常難得靠譜的人。”正如啟鈞所說,他們彼此熟識多年,了解對方的底線與價值觀念;這才促成了合作的默契,共同投入到民宿方面的創業中。
啟鈞向在座師生介紹了國内民宿行業的發展狀況。民宿行業的進程脈絡是:景區——鄉村——城市。其面臨的主要問題有三個:政策制約、收入模型、管理效率。由于國家政策在各地尚未落地,地區間的包容政策不一,導緻民宿行業發展受限。其次,民宿收入模型基本是以住宿為主,受波動的可能性較大。再者民宿行業的管理效率較之于酒店的管理略顯低下。然後啟鈞老師談到民宿的四個時代依次是利差、同質、服務、體驗。再者就是消費的不斷升級。消費逐漸從第一維度的基于品質,附帶價位發展到第二維度的從标準化到個性化,再到現今的第三維度精神層面上的。消費升級趨勢的倒逼使得民宿行業需要考慮“如何建構更有附加值的商業模型”等新問題。
回首過往,啟鈞感慨道“回顧我們非常平凡的三十幾年人生,可謂基本接受,難說青春無悔。”啟鈞以自身的豐富經驗向同學們表明了要時刻準備着,抓住低谷中的稻草與攀登新台階的機遇;同時,要學會堅持。